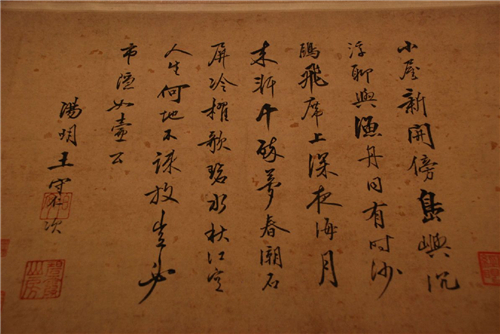根据王阳明的散文,我们能够感受到王阳明的自我形象,通过这些自我形象,我们也能够看出王阳明的思想、性格特征。
“勇者”形象
所谓勇者,也就是狂者,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而使自己身心受损,因此,王阳明散文的“勇者”自我形象塑造体现出他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不在乎外在的荣辱得失,不在乎别人的诽谤和侮辱,仅仅根据自己内心的情感和良知来处理问题。
嘉靖七年,王阳明接受当年皇帝的安排,负责到广西省镇压当时的部分乱臣贼子所进行的叛乱,他上《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》,在其中,他严厉地反对和讥讽了一些官员,“皆虞目前之毁誉,避日后之形迹,苟为周身之虑”,却没有考虑到自身的利益。
在这一时期,王阳明已经五十多岁了,却仍然具有着这样的尖锐的言辞。
通过古籍可以发现,王阳明从小的时候,就是一个说话算数、敢作敢当的男子汉大丈夫。而且,家庭因素也促进了王阳明的这种大智大勇的人格精神的形成。
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曾经做官,他的言辞也是非常直爽的。王阳明也是受到了他的父亲的遗传,从而更加促进了他的不贪图名利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的品格。
“隐者”形象
相对于王阳明散文的“勇者”自我形象塑造,就是王阳明散文的“隐者”自我形象塑造。这里的“隐者”并不是简单地回避世俗的隐者,而是负积极用世之意的隐者。
在王阳明前期的散文中,就能够体现出王阳明散文的“隐者”自我形象塑造。
在弘治十五年的《九华山赋》(王守仁,1992)657一文中,有下面的记载:“嗟有生之迫隘,等灭没于风泡;亦富贵其奚为?犹荣蕣之一朝。旷百世而兴感,蔽雄杰于蓬蒿。吾诚不能同草木而腐朽,又何避乎群喙之呶呶!”
这些文字充分体现出王阳明对于人的非常短暂的生命的感慨,显示出他消极厌世的情感。
在王阳明的散文的后期,他的思想开始转向圣贤之学,只读圣贤书,愿意做一个圣贤之人,展示出王阳明归隐田园的向往。
王阳明提出了良知说,在这一时期,是王阳明的思想最为成熟的时期,这一时期的散文也非常深刻地体现出王阳明的归隐思想,其主要原因如下所述。
首先,王阳明试图通过归隐田园来自适并奉亲,自适是因为他非常讨厌纷繁芜杂的外界环境,非常不喜欢官场的种种不端行为,王阳明在官场任职,就肯定会经常受到各种各样的非难排挤,并且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陷害。
通过王阳明前期的一些散文能够淋漓尽致地体现出这一点。例如,《九华山赋》中“又何避乎群喙之呶呶”,《对菊联句序》中“相与感时物之变衰,叹人事之超忽”。在正德十五年,王阳明所处的官场达到了令他生命非常危急的险恶状况。
其次,王阳明期盼能够在田园的生活中可以传道与授学。他希望能够摆脱繁杂的官场公务,能够一心一意去讲学。
他的确是要摆脱官场的限制和仕途的艰难困境,只是一心想着归隐田园,真正去欣赏自由洒脱的人生乐趣,在山清水秀的田园生活中施展自己的人生抱负,能够真正发挥出自己的才能。
但是,王阳明在追求一种心外无物的超然境界的过程中,却并没有忽视个人的人生重担。
他一方面必须准备着在朝廷需要他的时候能够随时出山为朝廷效力、为国家尽忠,另一方面,王阳明也会努力地为前来求学的士人讲学论道,来更好地最大限度的启发他们的良知,让他们能够具备坚定不移的求圣志向,实现自我的人生境界的提升,能够发挥出个人的真正作用,能够为国家尽忠,并且担负起拯救天下的责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