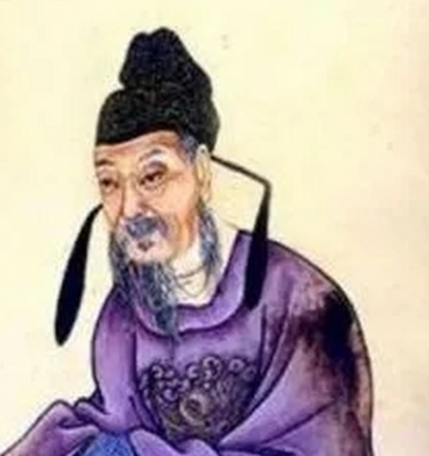唐玄宗天宝十四载(755年),安史之乱爆发。当叛军铁骑踏破洛阳城门时,东都御史中丞卢奕面对安禄山的屠刀,选择以血肉之躯捍卫气节。这位在《新唐书·忠义传》中位列榜首的忠臣,正是唐代奸相卢杞之父。卢氏家族三代清廉的仕宦传统与卢奕宁死不屈的壮烈,与卢杞的阴险毒辣形成鲜明对比,折射出人性在权力漩涡中的复杂嬗变。
一、清廉世家的政治基因
卢氏家族的仕宦传统可追溯至唐玄宗时期。卢奕之父卢怀慎官至黄门侍郎、同平章事,虽因“伴食宰相”的雅号被后世讥为庸才,但其清廉品格却载入史册。史载卢怀慎为官“器宇宏远,风神散朗”,虽位居宰辅却家徒四壁,病逝时连丧葬费用都需友人资助。唐玄宗亲撰碑文,称其“清慎贞素,不耀华腴”,这种“清节不易”的家风深刻影响了卢氏子弟。
卢奕之兄卢奂在任广州太守期间,面对岭南富庶之地的巨大诱惑,仍能“不染南金之利”,玄宗特赐金帛并题写“斯为国宝,不坠家风”的赞词。卢奕本人更是将这种清廉推向极致,史载其“谨愿寡欲,不尚舆马,克己自励”,任东都御史中丞时,连日常饮食都简朴至极。这种三代传承的清廉品格,使卢氏成为唐代官场中罕见的“清流世家”。
二、洛阳城头的血色抉择
天宝十四载冬,安禄山叛军攻陷洛阳。作为留守御史中丞,卢奕本可随唐玄宗西逃,却选择坚守衙署。当叛军将刀架在其颈时,卢奕厉声痛斥:“尔等逆天叛君,必遭天谴!”安禄山恼羞成怒,命人割其舌,卢奕仍以血唾其面。叛军将其首级悬挂于洛阳城门,百姓见之无不垂泪。
这种壮烈并非偶然。安史之乱前,卢奕已预感危机,曾密奏玄宗“河北藩镇跋扈,当早图之”。叛乱爆发后,他一面组织抵抗,一面暗中保护滞留洛阳的官员家属。其幕僚劝其暂避锋芒,卢奕却正色道:“吾家三代食禄,今国难当头,岂可苟全性命?”这种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气节,使其成为唐代忠臣的典范。
三、忠烈之血与奸佞之子的悖论
卢奕的殉国之举为卢氏家族赢得无上荣光。唐肃宗追赠礼部尚书,谥号“贞烈”,并命颜真卿撰写《卢奕神道碑》。然而,这种忠烈血脉在卢杞身上却发生了诡异变异。作为卢奕独子,卢杞凭借父祖余荫步入仕途,却逐渐显露出阴险毒辣的本性。
建中二年(781年),卢杞拜相后立即展开政治清洗。他设计逼死前宰相杨炎,诬陷忠臣颜真卿“谋反”,将其缢杀于蔡州。为聚敛钱财,他创设“间架税”“除陌税”,导致“天下怨声载道”。更令人发指的是,他竟利用唐德宗多疑的性格,诬陷功臣崔宁与叛军朱泚勾结,致其被缢杀于宫中。
这种悖论在唐代史书中引发激烈争论。《新唐书》将卢奕列入《忠义传》,却将卢杞归入《奸臣传》,形成鲜明对比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痛斥卢杞“面如蓝鬼,心如蛇蝎”,而欧阳修则感叹:“卢氏三代清节,何以生此逆子?”这种家族基因的断裂,成为后世研究人性异化的典型案例。
四、历史回响:家风传承的现代启示
卢奕的忠烈与卢杞的奸佞,揭示了权力对人性的腐蚀规律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指出:“德薄位尊,智小谋大,鲜不及矣。”卢杞虽出身清廉世家,却因缺乏道德约束,最终沦为权力怪兽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,卢奕之孙卢元辅继承了家族清廉传统,官至兵部侍郎仍“清行闻于世”,证明家风传承的关键在于道德自觉。
这种历史教训在当代依然具有警示意义。2025年某省纪委监委的调研显示,近五年查处的厅级干部腐败案件中,32%的涉案人员出身“红色家庭”或“清廉世家”。这印证了《论语》“富贵易失仁,贫贱难守节”的古老智慧,也凸显出家风建设必须超越血缘传承,建立制度化的道德约束机制。
卢奕的洛阳血泪与卢杞的澧州结局,构成了一部微缩的唐代兴衰史。当我们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凝视颜真卿书写的《卢奕神道碑》时,不仅能感受到忠臣的浩然正气,更应思考:在权力与欲望的漩涡中,如何守护人性中的光明?这个问题,或许正是卢氏家族故事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启示。